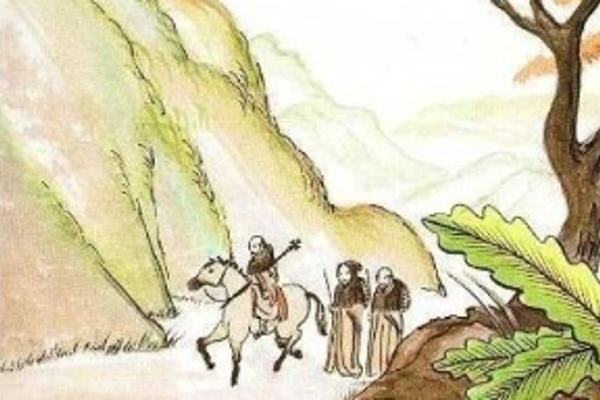2024
七月
31
【壹明头条】| 以传教视角审视中国的古老东方教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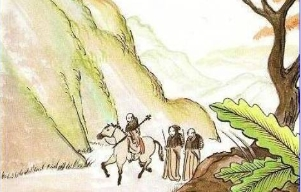
以下是信仰通讯社的社长于7月5日至7日在陕西西安举行的“西安国际景教论坛——2024东方叙利亚教会论坛”上发言的全文:
2022年秋天,我有幸在罗马采访了东亚述教会宗主教阿瓦三世罗耶尔。
现在,这个教会人数不多,但历史悠久,是古老东方教会的直接继承者。在基督信仰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东方教会是非同寻常的传教冒险的中心。因着这样的经历,将基督信仰传教活动从中东带到了阿拉伯半岛、印度,甚至中国。
采访中,我请阿瓦三世谈谈在他看来那次伟大传教冒险的秘诀是什么。这位年轻的亚述教会牧首回答说,古代东方教会的传教士是一支独特的“军队”、一支灵修大军。他进一步表示,传教士们主要是修士和修女,他们“以温和的方式,而不是以征服的动力”赢得了他人的心。“对他们来说,生活中的每一件棘手的事、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成为行善的机会,和每个人成为朋友和兄弟”。
我认为,这一非同寻常的历史和教会史实仍具有现实意义的原因有多个。我发言的大部分内容都要归功于意大利汉学家、波塞团体修士马泰奥·尼科里尼-扎尼(Matteo Nicolini-Zani)丰富而深入的研究。我主要是指他的《对话中的修行使命》一文,收录在《东方视角下的普世教会使命》一书中。这本书由耶稣会士杰尔马诺·马拉尼教授编辑、宗座传信大学出版社出版。
东方教会的起源和特性
自古以来,在中国扎根几个世纪之久的东方教会团体通常被称为“聂斯脱略派”。因为,431年召开的厄弗所大公会议上,君士坦丁堡宗主教聂斯脱略坚持继续与其本人所在的安提约基亚教会的神学和灵修传统保持联系而遭到了大公会议的谴责。安提约基亚教会传统强调基督的道成肉身和人性,即祂的人性,承认通过基督的人性揭示了祂神性的奥迹。
自公元3世纪初,东方教会便开始努力建立一个自主的教会,游离于罗马帝国疆界之外,与帝国教会保持距离。东方教会的基督徒们有自己的牧首,公署设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底格里斯河畔的塞琉西亚-凯西芬。
与帝国教会,特别是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教会拉开距离,并非主要出于神学或教义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我们可以广义上讲是出于政治原因。
随着东方教会逐渐东移,转向波斯帝国及其他地区——也是为了避免遭到迫害,这一团体还必须表明其基督徒不属于与罗马帝国有联系的群体。而几个世纪以来,罗马帝国一直是波斯帝国的头号敌人。
东方教会团体通过不同的途径和进程逐步向东方拓展。在某些情况下,是因为波斯帝国所征服领土上的人口被驱逐所致。而当时被驱逐的人中有基督徒,也有主教。
在局势相对平稳的时期,基督徒会沿着商贸路线向东迁徙。无论如何,在前往东方的途中,叙利亚教会的基督徒遇到了新的民族、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和新的宗教团体。
例如,他们到达今天的阿富汗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新的主教区时,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等城市成了游牧商人族群(中亚古代民族)索格迪亚纳人的聚集地。而这些商人,一部分成为基督徒。为了照顾索格迪亚纳商人的牧灵,祝圣了接受他们游牧民族特性的主教。
为此,叙利亚东方教会的基督信仰是随着历史事件(移民、驱逐、贸易流动)的演变而拓展的。
斯蒂芬·贝文斯(Stephen Bevans)和罗杰·施罗德(Roger Schroeder)在他们关于传教神学的主要著作中指出,这一“传教运动”的原创性和重要性与以下两个特点有关:
一是修行的内涵;二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对话态度。
修行的传教
叙利亚东方教会的传教活动主要是靠修士们的努力。在新的领土上,第一批团体始终都是围绕着修道院建立的。
被派去照顾这些团体基督信仰生活的传教士,甚至波斯领土外新教省的主教们,都是成长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波斯修道院中的修道士们。
史料显示,弟茂德宗主教曾派遣摩苏尔(今伊拉克)东北部贝特阿贝修道院的修士们到中国担任主教。
这些修道士在圣经研读和神学方面训练有素,因着他们的信德,已经做好了迎接艰难困境的准备。
弟茂德宗主教在一封信中写道:“许多修士们只拄着一根棍子、带着一个马鞍袋漂洋过海到印度和中国去”。
1625年,在距离西安市不远的周至教区发现了“景教流行碑”,现保存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它是考古文物,见证了早在公元635年,东方教会的传教士就来到中国,开始宣讲基督信仰。石碑建于公元781年,用中文和叙利亚文镌刻的正面碑文上写道“大秦景教中国流行碑”。汉语中,“大秦”一词最初仅指罗马帝国。后来,这个词被用来专指在中国永久定居的叙利亚教会团体。
碑文还表明,在古代东方帝国的首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也有修道院。
景教流行碑将基督信仰团体描述为一个具有修院特征的团体,其成员不为世俗的激情所左右、他们守斋和忏悔。按照修士的教规善度礼仪生活,每天祈祷7次,并从事爱德活动。
这种传教活动的另一个特点是开放和对话,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与文化对话、与宗教团体对话、与权势和政治当局对话。
与文化对话
东方教会的传教修士们来到这里后,并没有将自己置于强势地位,而是谦卑的修行人和商人。正因为他们的信仰和教义根基深厚,才能以对话的态度接触当地的文化和文学传统,就像基督信仰与希腊罗马文化相遇时一样。
唐朝(618-907年)和元朝(1272-1368年),叙利亚-东方团体在中国蓬勃发展。抵达中国后,传教士们面对的是一种超凡的文化。为了见证信仰,他们开始努力让基督信仰神学语言更加适应于中国文化背景,同时保留了安提约基亚信仰的核心。
即使在石碑碑文中,也大量引用了中国经典中的表达方式。
由此,修士们开启了一个汉化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将中国文化资料平铺直叙、机械地替换为东叙利亚的表达方式,而是一个更加渐进、更具生命力的融合过程。只有这样,适应才是名副其实的、富有成效的。
传教与宗教对话
根据东方教会在中国的经验,基督信仰的用词采用了佛教和道教等宗教方式和教义术语。甚至连描述寺院机构的词汇,如“寺院”,也取自佛教。他们的这一尝试所产生的文本中,许多关键术语都属于佛教和道教的宗教范畴。使用这种语言并不意味着会丧失基督信仰身份,而是在多元化背景下阐释基督信仰“本体”的一种方式。这是用希腊和罗马文化世界以外的文化背景中的词语来宣扬基督信仰的本质。例如:三位一体的奥迹是通过“光明教三尊”的救赎来表达的。
这种合成的影响还体现在一些史料记载中,例如:泉州基督教墓碑上的圣像(公元十三世纪)。这些墓碑中的十字架被嫁接到莲花上,天使般的天人则以佛教圣像画的模式绘制。
传教以及与政治和权力的对话
东方教会在中国传教所实践的对话方式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待唐朝皇帝和蒙古元朝统治者的权威和政治权力的态度。
为了获得儒家政治意义上的合法和“正统”教义的认可,与朝廷当局的持续对话堪称是一种必要的手段。这是基督信仰被中国社会接受的唯一途径,也是避免与被视为有害和变态邪教联系在一起,并受到法律制裁的唯一途径。
景教流行碑本身就证明了叙利亚基督信仰在中国朝廷中获得合法地位的意图。
整块石碑都充满了展示统治者正义行为与教会在中国存在之间的联系,以及和谐的意图,教会对社会秩序和共同利益做出了贡献。因此,碑文也见证了中国对信仰团体与政治当局之间关系的构想和处理方式的适应过程。
一些基督徒在大唐帝国的政治和军事管理要害部门担任官员和军官。
法国枢机尤金·蒂塞朗(Eugene Tisserant)是一位东方基督信仰问题专家和爱好者。他在一本关于东方教会的著作中指出,“在中国的景教神职人员自愿为政府服务,担任公职”。
这其中还包括了景教流行碑的建立者,波斯传教士伊斯。碑文中最后一部分介绍了他的生平,特别重点强调了他在朝廷中担任的高级职务,并颂扬了他践行基督信仰慈悲美德的事迹。
在这种与政治当局合作并为其服务的态度中,教会在与罗马帝国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中找到了自己的合法性。
基督信仰以其在中国团体的生活和见证方式,成为一种可以被接受的信仰。因为它不被视为外国人的教义,也不屈服于外国势力或利益。
多位基督徒在几个世纪前就已在中国担任参知政事和御史大夫的史实充分表明,在那个历史时期,选择对话而不是反对,对于传播福音和为福音作见证是有益的。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于多个世纪后殖民主义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结论
上面提到的两位学者斯蒂芬·贝文斯(Stephen Bevans)和罗杰·施罗德(Roger Schroeder)指出,古代东方教会的传教经验对我们现在有很多启示。对相遇和对话持开放的态度,可以追溯到传教的源头。而在当今世界,对话和开放的相遇态度越来越明显地成为所有基督徒见证的必要能力。一百年前,即1924年,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中国天主教全国教务会议也证明了这一点。今年5月21日,宗座传信大学和本社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特别纪念了这一重要的会议。
正如福音传播部初传和新地方教会部代理部长路易斯·安东尼奥·塔格莱枢机在纪念大会上指出的,福音的传播与一种文明和一种文化无关,恰恰因此保护和促进了各民族及其文化财富。因为耶稣带来的解放和治愈是给每个人的恩典,正如教宗方济各反复重申的。
——文章来自信仰通讯社